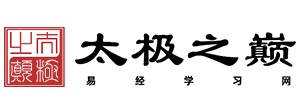【周易下經】第57卦-巽卦?巽卦為風(巽下巽上)-[明]楊爵《周易辯錄?卷四》

巽:小亨,利有攸往,利見大人。
剛,巽乎中正而志行。
九五以陽剛居中正之位,而其志可行,所謂中天下而立,定四海之民也。初六順乎九二,六四順乎九五,則柔皆順乎剛。用事者為陽剛君子之類,而隂柔之小人歸於從伏之下,而不得行其志,故可以小亨,而利有攸往,利見大人。其不能大亨者,何也?凡陽剛之才之作用,可以大有為而致大亨。巽體本隂,而重巽則巽之。巽,隂之隂者也,固不能大有為而致大亨也。治道不能如三代者,僅為小康而已。施為不法乎三代者,溺於陋習而已。如漢唐之治,皆為小亨小康,而己其利有攸往,亦不出乎雜覇雜夷之作用也。比於三代聖王井田、封建、學校之制,對時育物,舉一世而甄陶之,則如天地之相懸矣。
九五以剛陽居尊,有大人之象,見之而得以行其所學,亦君子所願也。此亦巽之大人也,比之與天地合德之大人,則有間矣。如漢文帝、唐太宗,亦可謂當時之大人矣。然德未至於盛,則治未至於極,效止庶富,而禮樂不興,可以當此之小亨也。重巽言申命,隨風則言申命,行事申命,皆取重巽隨風之義,申命後必有所事也。申者,丁寜告喻之也。或以己之所行諭民,知之而後行之,或命民以所當行之事,既命之後即令民行之,上之人視其所行之勤惰而勸懲之,亦行事之義也。
初六當巽之時,以隂居下,過於柔懦而不能振拔者也。事多失之不及,為或進或退而不能果決之象,利於武人之貞焉。武人而非貞,則血氣之強而已矣。惟能貞也,則凡剛毅果斷而振奮有為者,皆純於義理之正而為君子所尚矣。初非能此,聖人因其柔之甚而激勵之,使志於治也。古人有以性緩而佩弦者類此。
九二巽在牀下,過於巽者也。史巫之紛若,所以逹誠意於神明也。用史巫紛若,用其誠也。能用其誠,則凡過於巽者皆真德實意,而非足恭之虛貌,則可以得吉矣。二有剛中之德,其巽可以合於道,故聖人勉之以用誠焉。非誠則其巽為象恭行詐之小人,而君子之所羞見者也。
九三剛正,居下之上,巽本可以得正也。然處六四之下,四隂柔,其性務入而近於五,是夤緣鑽刺、得時得志之小人也。三居其下,朶頤於其勢而數巽焉,可羞之甚也。所得者富貴,所喪者名節,廉恥之不修而其志亦窮矣。
六四以柔居柔為得其正,當巽之時,近於五能巽於五者也。位在一人之下、萬人之上而能巽於五,庶幾乎夔夔然存敬畏之心者也。如此則道可行於五,而功被於上下矣。為田獲三品大有功之象,其過巽之悔,至是可以亡之矣。自九三視六四,則四為容悅諂諛之小人,所以戒三之遠乎四也。至是則又以四為?恭寅畏之大臣,所以勉四之忠於五也。或抑或揚,取各有所指。
九五以巽體居尊位,所不足者貞而己,故勉之以能貞,則可以得吉於柔懦不能自立之悔,可以亡之,而所為無不利矣。有悔是無初也,以能貞而亡之,是有終也。然所謂貞者,不過於惇典庸禮,命德討罪,合於天理,當於人心,而不參以私意於其間,則貞之至也。是道也,毫忽幾微之不察,則流於失而不自知矣。故必丁寜揆度,詳審周密,而戒之至,則動無過舉,可以得其當而吉矣。先庚三日,後庚三日,即貞之義也。
上九居巽之極,為過巽之甚,巽在牀下之象也。陽剛本能斷者也,而過於巽焉,則失其剛斷之德,為喪其資斧之象也,其為害誠不細矣。雖為所當為,而以優柔不斷處之,亦必兇,況所不當為者乎?蓋無適而非兇也。執狐疑之心,持不斷之謀者,上九之謂也。所以來讒慝之口,啓羣枉之門者,皆由於此。故象言其正乎兇,君子可以深戒矣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