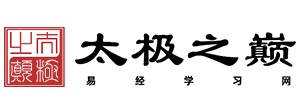【周易下經】第41卦-損卦?山澤損卦(兌下艮上)-[清]李光地《御纂周易折中?卷第六》

程傳:《損·序卦》:“解者緩也,緩必有所失,故受之以損。”縱緩則必有所失,失則損也,《損》所以繼《解》也。為卦艮上兌下,山體高,澤體深,下深則上益高,為損下益上之義。又澤在山下,其氣上通,潤及草木百物,是損下而益上也。又下為兌說,三爻皆上應,是說以奉上,亦損下益上之義。又下兌之成兌,由六三之變也,上艮之成艮,自上九之變也,三本剛而成柔,上本柔而成剛,亦損下益上之義。損上而益于下則為益,取下而益于上則為損,在人上者,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,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。譬諸壘土,損于上以培厚其基本,則上下安固矣,豈非益乎。取于下以增上之高,則危墜至矣,豈非損乎。故損者,損下益上之義,益則反是。
損,有孚,元吉,無咎,可貞,利有攸往。
本義:“損”,減省也。為卦損下卦上畫之陽,益上卦上畫之陰。損兌澤之深,益艮山之高。損下益上,損內益外,剝民奉君之象,所以為損也。損所當損,而有孚信,則其占當有此下四者之應矣。
程傳:“損”,減損也。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,皆損之道也。損之道必有孚誠,謂至誠順于理也。損而順理,則大善而“吉”,所損無過差,“可貞”固常行,而利有所往也。人之所損,或過或不及,或不常,皆不合正理,非有孚也。非“有孚”則無吉而有咎,非“可貞”之道,不可行也。
集說:呂氏大臨曰:《損》之道不可以為正,當《損》之時,故曰“可貞”。時損則損,時益則益,茍當其時,無往而不可,故《損》、《益》皆“利有攸往”。
蔡氏清曰:剝民奉君之義,只可用之卦名,其卦辭“有孚,元吉,無咎,可貞,利有攸往”,只承損字泛說。言損所當損,人人皆可用,不專指上之損下也。《益》卦“利有攸往,利涉大川”亦然,豈專為益下之事乎?
曷之用,二簋可用享。
本義:言當《損》時,則至薄無害。
程傳:“損”者,損過而就中,損浮末而就本實也。圣人以寧儉為禮之本,故為損發明其義。以享祀言之,享祀之禮,其文最繁,然以誠敬為本,多儀備物,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,飾過其誠,則為偽矣。損飾,所以存誠也,故云“曷之用,二簋可用享”。“二簋”之約,可用享祭,言在乎誠而已,誠為本也。天下之害,無不由末之勝也。峻宇雕墻,本于宮室。酒池肉林,本于飲食。淫酷殘忍,本于刑罰。窮兵黷武,本于征討。凡人欲之過者,皆本于奉養,其流之遠則為害矣。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,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。《損》之義,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。
集說:孔氏穎達曰:“曷之用二簋可用享”者,明行損之禮。貴夫誠信,不在于豐,“二簋”至約,可用享祭。
案:彖辭自“有孚”以下,泛說《損》所當損之義,蔡氏之說,極為得之。蓋損益者時也,時在當損,不得不損,唯以誠意為主,而行之又得乎大善之吉,則不但“無咎”,而且可以為常道而利有所往矣。舉一端以明之,則如“二簋”薄祭,固因乎時而節損者也。然能積誠盡禮,則可以致孝乎鬼神,而推之凡事之當損者視此矣。卦義以孚而行損,《程傳》則因損以致孚,略有不同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初九
初九,已事遄往,無咎,酌損之。
本義:初九當損下益上之時,上應六四之陰,輟所為之事而速往以益之,“無咎”之道也,故其象占如此。然居下而益上,亦當斟酌其淺深也。
程傳:損之義,損剛益柔,損下益上也。初以陽剛應干四,四以陰柔居上位,賴初之益者也。下之益上,當損己而不目以為功。所益于上者,事既已則速去之,不居其功,乃無咎也。若享其成功之美,非損己益上也,于為下之道為有咎矣。四之陰柔,賴初者也,故聽于初。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己以益之,過與不及,皆不可也。
集說:孔氏穎達曰:損之為道,損下益上,如人臣欲自損己奉上。然各有職掌,若廢事而往,咎莫大焉。竟事速往,乃得無咎。酌損之者,以剛奉柔,初未見親也,故須酌而減損之。
《朱子語類》云:酌損之,在損之初下,猶可以斟酌也。
案:孔氏說已事之義,謂如學優而后從政之類,于理亦精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九二
九二,利貞,征兇。弗損益之。
本義:九二剛中,志在自守,不肯妄進,故占者“利貞”,而“征”則“兇”也。“弗損益之”,言不變其所守,乃所以益上也。
程傳: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,居柔而說體,上應六五陰柔之君,以柔說應上,則失其剛中之德,故戒所利在貞正也。“征”’行也。離乎中,則失其貞正而兇矣,守其中乃“貞”也。“弗損益之”,不自損其剛貞,則能益其上,乃益之也。若失其剛貞,而用柔說,適足以損之而已,非損己而益上也。世之愚者,有雖無邪心,而唯知竭力順上為忠者,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。
集說:林氏希元曰:九二在爻則為剛中,在人事則為志在自守,不肯妄進。志在自守,不肯妄進,九二之貞也,故占者利于守貞。若征行,則是變其所守而得“兇”矣。夫自守而不妄進,宜若無益于上矣。然由是而啟時君尊德樂道之心,止士大夫奔競之習,其益于上也不少,是弗損乃聽以益之也。桐江一絲,系漢九鼎,清風高節,披拂士習,可當此爻之義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六三
六三,三人行,則損一人,一人行,則得其友。
本義:下卦本乾,而損上爻以益坤。“三人行”而“損一人”也。一陽上而一陰下,“一人行”而“得其友”也。兩相與則專,三則雜而亂,卦有此象,故戒占者當致一也。
程傳:“損者”,損有余也。“益”者,益不足也。“三人”,謂下三陽上三陰,三陽同行,則損九三以益上,三陰同行,則損上六以為三,“三人行則損一人”也。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,但言其減一耳。上與三雖本相應,由二爻升降,而一卦皆成,兩相與也。初二二陽,四五二陰,同德相比,三與上應,皆兩相與,則其志專,皆為得其友也。三雖與四相比,然異體而應上,非同行者也。三人則損一人,一人則得其友。蓋天下無不二者,一與二相對待,生生之本也。三則余而當損矣,此《損》、《益》之大義也。夫子又于《系辭》盡其義曰:“天地絪緼,萬物化醇,男女媾精,萬物化生,《易》曰:“三人行則損一人,一人行則得其友”,言致一也。”“絪緼”,交密之狀。天地之氣,相交而密,則生萬物之化醇。“醇”,謂醲厚,醲厚,猶精一也。男女精氣交媾,則化生萬物。唯精醇專一,所以能生也。一陰一陽,豈可二也。故三則當損,言專致乎一也。天地之間,當損益之明且大者,莫過此也。
集說:林氏希元曰:此爻之辭,兼舉六爻,以三正是當損之爻,乃卦之所以為《損》者,故于此言之。
楊氏啟新曰:人之相與,唯其心之同而已。茍精神不孚,意氣不貫,則群黨比周,固三也。即一人之異,亦三也,是皆不可以不損也。茍精神相孚,意氣相貫,則二人同心,固兩也。即千百其朋,亦兩也,是皆不可以不得者也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六四
六四,損其疾,使遄有喜,無咎。
本義:以初九之陽剛益己,而損其陰柔之疾,唯速則善,戒占者如是,則“無咎”也。
程傳:四以陰柔居上,與初之剛陽相應,在損時而應剛,能自損以從剛陽也,損不善以從善也。初之益四,損其柔而益之以剛,損其不善也,故曰“損其疾”。“疾”,謂疾病,不善也。損于不善,唯使之遄速,則“有喜”而“無咎”。人之損過,唯患不速,速則不致于深過,為可喜也。
集說:王氏弼曰:履得其位,以柔納剛,能損其疾也。疾何可久,故速乃“有喜”,“有喜”乃“無咎”也。
蘇氏軾曰:“遄”者初九也,“損其疾”,則初之從我也易,故“遄有喜”。
楊氏萬里曰:六四以柔居柔,得初九之陽以為應,“損其疾”者也。初言”遄往”,四言“使遄”,蓋初之“遄”,實四有以使之也。
胡氏炳文曰:六四與初九為應,初方已其事而速于益四,四損其陰柔之疾,唯速則“有喜”。不然,彼方汲汲,此乃悠悠,非受益之道。
又曰:下損己以益上,當使下亦速有所喜,乃“無咎”。
案:蘇氏,楊氏說,于使字語氣亦近是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六五
六五,或益之,十朋之龜。弗克違,元吉。
本義:柔順虛中,以居尊位,當《損》之時,受天下之益者也。兩龜為朋,十朋之龜,大寶也。或以此益之而不能辭,其吉可知。占者有是德,則獲其應也。
程傳:六五于《損》時,以中順居尊位,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,是人君能虛中自損,以順從在下之賢也。能如是,天下孰不損己自盡以益之,故或有益之之事,則十朋助之矣。“十”,眾辭。“龜”者,決是非吉兇之物。眾人之公論,必合正理,雖龜筴不能違也,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。古人曰:謀從眾則合天心。
集說:張子曰:龜弗能違,言受益之可必,信然不疑也。
楊氏時曰:柔得尊位,虛己而下人,則謙受益。時乃天道,天且不違,況于人乎,況于鬼神乎,宜其益之者至矣。故曰“或益之十朋之龜,弗克違,元吉”。
郭氏雍曰:《益》之至,豈獨人事而已,雖元龜之靈弗能違,此其所以“元吉”也。《洪范》曰:汝則從,龜從筮從,卿士從,庶民從,是之謂大同,六五之“元吉”,猶《洪范》之“大同”也。
楊氏簡曰:“或”者,不一之辭。“益之”者,不一也,人心歸之也。“十朋之龜”,皆從而弗違,天與龜神祐之也。龜神祐之,故“龜筮協從”。
御纂周易折中卷第六:損卦上九
上九,弗損益之,無咎,貞吉,利有攸往,得臣無家。
本義:上九當損下益上之時,居卦之上,受益之極,而欲自損以益人也。然居上而益下,有所謂惠而不費者,不待損己,然后可以益人也。能如是則“無咎”,然亦必以正則“吉”,而利有所往。惠而不費,其惠廣矣,故又曰“得臣無家”。
程傳:凡《損》之義有三,損己從人也,自損以益于人也,行損道以損于人也。損己從人,徙于義也。自損益人,及于物也,行損道以損于人,行其義也。各因其時,取大者言之,四五二爻,取損己從人,下體三爻,取門損以益人,損時之用,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。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為義,九居損之終,損極而當變者也。以剛陽居上,若用剛以損削于下,非為上之道,其咎大矣。若不行其損,變而以剛陽之道益于下,則“無咎”而得其正且“吉”也。如是則宜有所往,往則有益矣。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,天下孰不服從,從服之眾,無有內外也,故曰“得臣無家”。“得臣”,謂得人心歸服。”無家”,謂無有遠近內外之限也。
集說:王氏肅曰:處《損》之極,損極則益,故曰不“損益之”。“得臣”則萬方一軌,故“無家”也。
句氏微曰:上九剛德,為物所歸,雖曰“得臣”,非已所有,蓋以四海為家。
《朱子語類》云:“得臣”有家,其所得也小矣,“無家”則可見其大。
案:卦以損三益上成義,則上者受益之極,卦之主也。故“尤咎,可貞,利有攸往”之辭,皆與卦同。其不言“有孚元吉”者,弗損于下而有益于己,此非有至誠仁愛之心者不能也。蓋黎民之生厚,則所以固本寧邦者至矣,仁義之俗成,則其有遺親后君者鮮矣,其為益孰大于是。然其不損于下者,乃所以自損于己也,此所以合乎卦義有孚元善之德也。“得臣無家”,則又極言“弗損”之規模。與夫獲益之氣象,自其弗損之心而言之,為天下君而不自利于己,自其得益之量而言之,莫匪王臣而不視為私屬,皆所謂“得臣無家”,王道之至也。蓋五上二爻,相蒙為義。五之虛中,既已格乎鬼神,而獲“元吉”,則彖所謂“有孚元吉”者已備。故于此爻,遂究其說,以終其義也。九二之“弗損”,謂損己。“益之”,謂益人。此爻之“弗損”,謂損人。“益之”,謂益己。辭同而指異者,卦義損下益上,故在下卦為自損,在上卦為受益。
卦名以損下益上為義,卦辭則泛論損所當損,而損中有益也。六爻之辭,其以上下體分損益,則根乎卦名,其言損所當損,而損中有益,則又根乎卦辭。